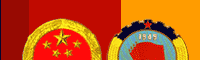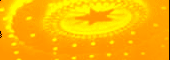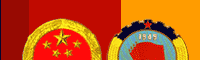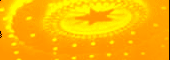“今年我国国债增发量将从去年的1500亿元降为1400亿元。从今年开始,在我国实施了长达5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减弱力度并平稳淡出”、“实施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随着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的上任逐渐淡出”……
“两会”前,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将要淡出的趋势预测并不鲜见,然而,二OO三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公布后,尤其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3月8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其透出的信息已非常明确:如果加上去年结转的100亿,今年1400亿的国债发行规模并不少于去年。用王春正的话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也不是短短的几年,至少来讲是一个中短期的政策措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确实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病没医好,怎能停药
探讨积极财政的未来走向,大概永远也绕不过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不是能够长期执行下去?二、如果淡出,经济增长靠什么拉动?
其中,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简单、明了,也比较容易公开见到:从国际的经验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化。
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却并不太好说,也不太好听:由于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并未恢复,如果让积极的财政政策“全身而退”,拿什么来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目标?
“病没医好,怎么能停药?”东北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吕炜对记者说,“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已经不单是一项财政政策问题。由于受制于诸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加上世界经济前景预期总体不佳,未来一段时间里经济是否能较快恢复自主增长能力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可能性不大。”
吕炜教授坦言,积极财政政策的难以淡出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最大隐忧,因为这项政策由短期应对而转为中长期取向的固化趋势,所反映的实质是经济自主增长机制难以恢复、财政体制承载能力日益下降两大潜在风险。从连续实施五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来看,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直接拉动经济总量、防止经济失速方面,而作为政策目标的疏导经济循环、启动增长机制的任务完成得并不理想。
“正是由于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制约了市场机制自运行能力的重新启动,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只能局限于治标,达不到治本的目的,财政逐渐演化为目前这种经济运行特征的一个内生因素,无法顺利退出”,吕炜说。
药到病未除,体制因素是关键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目前,经济中的诸多矛盾正呈现出向财政集中转化的趋势,原本只是对付亚洲金融危机的反周期调控“应急措施”,5年过去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越来越“无奈地”流露出向中长期演变的趋势:
淡出,需求不足仍未解决,经济增长无法保障;不淡出,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财政风险不能不扛。很显然,积极财政的淡出要服从经济发展的大局,而财政政策的矛盾亦成为考察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窗口,其矛盾的根源正在于体制。
“积极的财政政策连续实施五年后,逐步在财政政策和经济运行之间形成了两种惯性”,吕炜分析说。
一种是经济总量增长的压力向财政政策收敛。由于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始终未能恢复,财政的扩张性拉动政策一直是国债投资到经济增长的应急、反射式的直接推动。1998年以来国债投资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9.2%、28.2%、21.3%、24.7%,2002年预计贡献率为25%。经济增长对财政政策依赖的成瘾性趋势,一方面使银行风险通过国债吸纳向财政转化,项目投资风险通过计划安排而确定了财政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另一方面财政自身在支撑经济增长中的运行风险也迅速加大。
第二种惯性是经济结构固化、强化的矛盾向财政政策收敛。在国债直接拉动的扩张性投资过程中,过去一直着力调整的一些重大经济结构出现固化趋势:
一是所有制结构固化问题。1998-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3.9%、5.1%、9.3%、12.1%;国债投资占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9%、75.9%、54.3%、35.1%;国有及其他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固定资产增加额的比例关系分别为81.19.89.1、58.710.131.2、71.014.414.5、72.910.516.6。三项数据表明,民间投资的不确定性很大,国有部分的投资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并逐渐改变着固定资产的存量结构。
二是地区结构固化问题。在投资总量扩张的同时,各地为应对经济滑坡、增加就业,纷纷扩大了地方性投资,放松了某些项目的审批环节,以支持发展和新建地方性的支柱产业,使得小规模、低水平、重复性投资上升,投资不经济问题变得突出。
三是产业结构固化问题。由区域性重复建设和其他因素引起的是钢材、玻璃、水泥等行业扩张过快、房地产投资出现局部过热的问题,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有所固化。从中长期看,一旦拉动作用放缓,过剩问题会更猛烈地爆发出来,投资不经济所导致的资产处置、资金链紧张、职工就业等问题又会成为巨大的包袱,财政既被看作是始作俑者,又必将是最终矛盾的化解人。
药方要添四味药
既然根本性的制约来自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冲突,那么治本之策必将着眼于深化改革,但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经济的运行不可能先停下来等待,目前的矛盾也需要暂时性的应对之策。
“因此,总体上仍要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通过治标之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较好的改革环境”,吕炜说,“治标与治本的结合实质上是政策与体制的搭配问题,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有以下四个关系需要妥善加以处理”。
为此,他给积极财政的药方又添加了四味药:
一、处理好财政政策创新与财政体制改革的关系,核心问题是解决好财政体制的承受力。
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建立的财政体制框架下运行的,由于几年内迅速实现了“两个比重”的提高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新的财政体制为承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因此财政体制改革的主体是成功的。但是也有不完善之处,突出表现在省以下财政体制不规范,财权、事权关系不明确,和中央财政实际可支配财力有限,宏观调控能力不足两方面,在实际运行中逐渐暴露出地区差距拉大、宏观平衡能力不足、部分县乡财政困难加剧的问题。这种不完善的体制在承载积极财政政策连续高强度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县乡和中央两级财政收支矛盾激化,财政债务负担的迅速增加。下一步要使扩大支出的政策继续得以落实,必须配合以完善财政体制的改革措施,增强体制的承载能力,实现中央财政和全国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二、处理好财政投资与供给结构改善的关系。
扩大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失速的核心内容,但在民间投资不活跃、不稳定的情况下,国有部分的投资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并逐渐改变着固定资产的存量结构,从而使所有制结构出现固化和强化的趋势,可能会影响到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资本的进退。同时在投资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各地为了应对经济滑坡、增加就业,纷纷扩大了地方性投资,放松了某些项目的审批环节,以支持发展和新建地方性的支柱产业,使得小规模、低水平、重复性投资上升,投资不经济问题变得突出。这可能会形成财政政策实施影响供给政策改善的局面。
实际上,连续五年的国债投资后,进一步扩大投资既面临着选项上的困难,同时也面临着地方配套上的困难。以投融资体制改革来改善财政政策与供给政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继续发挥政策效果的一项重要工作。调查发现,一些地方迫于配套搞建设的压力,不得不以国债资金为资本金进行公司化运营,通过国有或民营股份公司来募足剩下的建设资金。这种被迫的选择倒是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以国债资金引导民间投资、以市场的方式运作项目,既避免了对民间投资的挤出,又分散了项目投资失误可能产生的政府风险、银行风险。
三、处理好分摊转轨成本与发挥收入政策效应的关系。
旧的社会契约的限制,使刺激消费的政策大打折扣,日益突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既影响着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又吃掉了大量的财政支出。解除旧的社会契约的成本分摊会同时影响到个人消费和财政支出,但这些潜在的成本实际早已固化在过去的资本积累和资产形成中,因此原则上不应由现在的当期收入来支付,而应通过过去资产的处置与转让收益来进行历史补偿。比如在社会保障基金方面,现在的国有资产存量中有一部分是过去职工的社保基金形成的,在国有资产处置过程中,这一部分历史欠账原则上应该进行归位和补偿。按照这一思路,对国有资产的处置与经营将是化解这一系列矛盾的中心环节,只有尽快确立合理的解决方案,在居民未来支出中变得可以预期和可以承受,财政的收入政策才能转化为消费需求的提高。目前主要靠财政在当期支出中安排和通过增加个人收入的办法应对转轨成本的作法,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消化过程,也直接影响到消费的增长。
四、处理好收入差距与发展战略的关系。
在继续实行非平衡的改革与发展战略的同时,应积极关注和帮助低收入群体、逐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适当措施实现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带来的成果。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即正视中国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已经拉大的现实,将“富”与“贫”均视为可激活和转化为积极因素的中性变量,而不是静态、孤立地评判谁是消极因素、谁是积极因素,在支持、鼓励“富”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研究如何通过消费政策、投资政策构建起国内的产业转移、梯度推进战略,使“富—贫”之间产生动态的收入增长效应。通过“贫”、“富”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迅速整合存量资源基础上大范围调整和优化国内市场结构和总体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