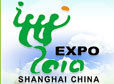1946年逝世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上周辞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由于弗里德曼曾花费大量精力抨击凯恩斯留下来的学说,人们自然会认为他们是相互对立的。的确,他们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别,但两者的共同之处亦是如此。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是赢家,也不是输家:今天的正统经济政策,是两人学说的综合体。
凯恩斯从“大萧条”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由市场已宣告失败;弗里德曼则认定:失败的是美联储。凯恩斯相信像他自己那样思想深邃的政府官员的判断力;而弗里德曼认为,只有受到严格规范制约的政府才是“安全”的。凯恩斯认为,需要对资本主义加以束缚;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若放开手脚,资本主义将呈现恰当行为。
这些差异不言自明。但双方的相似之处同样明显。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记者、辩论家和自身观点的倡导者。两人都认为,从根本上讲,大萧条是一场总需求不足导致的危机;他们都撰文支持浮动汇率,支持名义(或法定)货币;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重大斗争中,两人都站在自由的一边。
但凯恩斯虽然从气质上讲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也是一个江河日下的国家里,中上阶层的悲观一员:他认为,要保留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要放弃19世纪正统理念的许多要素。而弗里德曼作为贫穷的犹太移民之子和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较为乐观:他希望重振自由市场,并对政府进行限制。
为实现这一目标,弗里德曼试图推翻在他看来凯恩斯及其继承者所犯下的错误:从当前收入进行消费的固定倾向推动总需求这一假设;认为财政政策是最有力的政策工具这一想法;相信名义需求的变化将导致实际产出的持续变化;对政府运用其判断力抱有信心等。
备受争议的弗里德曼论
上世纪60年代,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的信奉以及对凯恩斯理念的反对是邪恶、误入歧途的,甚至两者兼而有之。70年代的大幅通货膨胀――和平时期的空前水平改变了舆论气候。1971年固定汇率体系崩溃,并转向浮动汇率体系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这一转变发生在价格飙升之前。
在这个汇率或多或少地自由浮动,而通胀急剧上升的世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提供指引。当时人们寄希望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以货币供应为指标。美联储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于1979年至1982年在美国尝试了这种做法。玛格利特·撒切尔当政时的英国政府也于1979年至80年代中期,进行了此种尝试。在这两次尝试中,通胀都被摧毁,但货币与名义需求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崩溃。凯恩斯理论的确已经死亡。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主导地位也同样逝去。
受规则约束的决策机制
其后,一种新正统学说从废墟中兴起: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经济政策应瞄准一个名义变量目标,而非实际变量目标;目标应当是通胀这一目的,而非货币这一手段;为了实现目标,各国央行应根据需要自由地调控利率。这就成了一种受规则约束的机断决策机制。弗里德曼赞成遵循规则;而凯恩斯赞成机断决策。弗里德曼胜在将货币政策置于首位;而凯恩斯胜在拒绝接受数量理论。
但从最重要的意义上讲,两人都获得了胜利。过去20年间,名义货币主导的世界做到了通胀水平适度,并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支撑。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弗里德曼本人今年初曾表示:“艾伦·格林斯潘的伟大成就在于,他证明了维持物价稳定的可能性。”这是一位伟大的规则倡议者,对一位伟大的机断决策运用者的赞誉。
以通胀为目标的独立的央行和自由浮动的货币,是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终结”呢?笔者觉得不是。浮动汇率的反复无常,似乎在呼唤另一次货币一体化实验,甚至尝试一种全球化的货币。
科技进步甚至可能使货币变得多余,使其仅限于发挥记账单位的作用。
政策辩论也将继续。欧洲央行或许终将说服它的同行,让它们相信货币数据给人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同样,各国央行或许也会认识到,它们忽视资产价格的行为存在风险。甚至可能还会再度出现对扩张型财政政策的需求,正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通缩时期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
同样不确定的还有市场经济的未来。两人目前在这方面打成平手。凯恩斯可能会担心,放开资本流动可能产生影响经济稳定的后果。而弗里德曼则不得不承认,全面缩减政府角色,并不在议程上。市场的确已经摆脱了20世纪中期的许多桎梏。但政府控制着资源,调控着经济,其程度在一个世纪前是无法想象的。全球化本身也可能失败。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是上世纪那场政策辩论的主角。但我们今天看到,他们既不是赢家,也不是输家。
《国际金融报》 (2006-11-28 第04版)
责编:韩军